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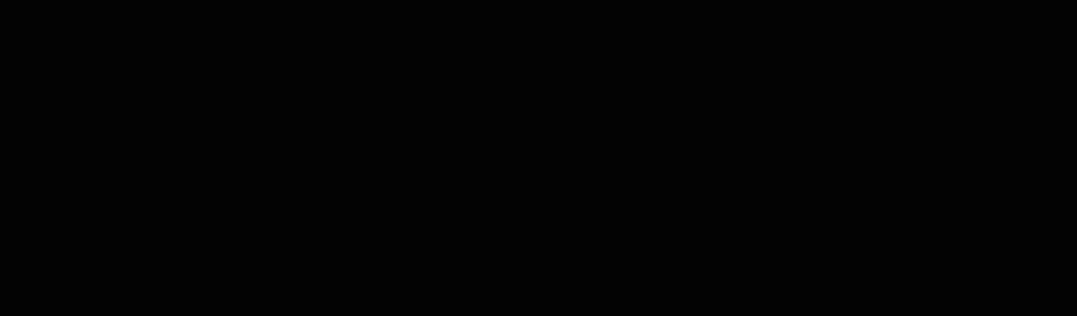

采访 李莱拉
编辑 刘敏
从2020年的冬天开始,作家班宇开始每天早晨从家步行十五分钟前往另一个地方。那是一个小的房子,在沈阳铁西区的一栋高层住宅,19楼,朝北,能看见日落。房子大约三十多平米,一个通体的开间。进门是厨房,台面上放着一口炒锅,一个小的煮蛋器。然后是客厅,灰色皮质沙发上卷起一床棉被,一个大型的白色宜家书架,底层放着波普乐和自由爵士的黑胶唱片,还有一台德国清澈牌黑胶唱片机。最后是桌子,电脑和键盘。窗外是沈阳高高低低的楼房。
班宇在这里度过了接下来的两年:看书,写作,隔离,看书,写作,感染新冠,隔离,康复。这个房间就像他在变动中维持自我的洞穴。
视频中,班宇状态不错,还是圆润的一张脸庞。我们的访谈推迟了半个月,那时他正感染新冠,嗓子嘶哑,无法说话。他打字讲,高烧后第一天嗓子疼到只能睡着十五分钟。担心感染女儿,他搬到小房子——也是他称呼的“工作室”里自我隔离了一阵,没回家,每天凑合做一顿面条或者饺子,或者用煮蛋器蒸些米饭和别的。情绪不佳时,他听黑胶唱片,吃在短视频软件上买来的乐事薯片大礼包,以及阅读。最近他在读《信号》和户川纯的随笔集。直到痊愈。他说,沈阳的感染高峰仍未过去,他总是在朋友那里听说一些与死亡相关的故事。
我上一次见到班宇是在2019年的夏天。那时他出版了第一本小说《冬泳》。我与他一起前往沈阳的工人村,天气灰蒙蒙的,我们围绕着老旧的苏式楼房,在公园和街道上行走。他谈到小说和现实的交缠,那些印厂机器卷走胳膊的工人、追债的年轻人和生疏的赌徒,人在历史中的隐喻,以及失落的东北。那是东北站在注意力高峰的一年:东北文学,还有《野狼disco》,二手玫瑰。有人说这就像一场“东北文化复兴”。
也许趁着这阵风,或者班宇本身成为了风的一部分,他像梦游一样参观了一圈名利场。明星易烊千玺和李健推荐了他的书,奖项和名声一同到来。后来在一次时尚杂志举办的宴会上,我看见班宇穿着借来的名牌西装,不安地松了松紧绷的领带。
然后是2020年,一切都改变了。班宇回到沈阳,结束了在中国各个城市做活动的跌宕日子。接着他辞去做了十多年的古籍出版社的工作,全职写作。除去陪伴家人,多数时间他都待在那个小房子里。不过说实在的,即使他尽力想维持一种规律的生活,他依然会有强烈的消耗感。有时他喝些酒,回到房子里,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,只能看些书,人就像一下子松垮下来。尤其是在2022年,他只写了四五篇小说。他能记起这三年里大大小小的公共事件,但与此同时,个人的时间和印迹却是模糊的。
他比喻说,就像是一团脏抹布,什么都擦不干净,眩晕的三年,现在还没法解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
不过他依然在写作,即使是缓慢的。他写完了《逍遥游》,现在又出版了新书《缓步》。《缓步》收录了九篇小说。其中有他在2018年写的,也有的在2022年年初才完笔。
在《缓步》里,他依然写到东北那些下岗的人,离异的人,在生活中卡顿的人。他也写到母女关系,以及人物情节都很模糊的“元小说”。一个显著的变化是,东北作为文学背景出现的次数正在变少,在那些东北消失的篇目里,班宇标志性的短句和方言也消失了。班宇说,他开始感到东北作为一种叙事外壳正在逐渐失效,他不再能召唤回一些对过去澎湃的感受。
这与现实相关吗?他也不清楚,只是这三年的时间里,似乎人们的处境在地域上的差别并没有那么显著。“我们难道不是经历了同样的政策吗?”
而他正在试图寻找新的写作重心,以及更重要的,寻找回生活的重心。
我开始不想讲东北那些故事了
那样热烈的感觉我无法再召唤回来
先生制造:让我们先来谈谈你的新书《缓步》。似乎和《冬泳》、《逍遥游》相比,这本书的东北性弱了很多。几乎有一半篇目都不再以中国的东北作为文学背景,似乎你在尝试一些新的风格。这背后的变化是出于什么原因?你觉得《缓步》这本书有一个统一的命题吗?
班宇:我有一个感受,就是我想把我写过的小说抛下。我之前和朋友开玩笑,这三部是不是“海陆空三部曲”,把三部曲做完了,赶紧把这些小说扔在身后,我好能做新的想做的事情。
不过的确《缓步》这本书比前两部所谓的命题性都要模糊。它的跨越时间很长,不像前两部都是在一年内写好的。这本书里的短篇有在2018年写的,也有的在2022年初才完成。这就和我们的生活在这几年的变化一样。它里面的情绪不太恒定,也就不太具备一个真正主题的统摄。如果非要总结,也许可能是谈到一点中年感,大约是说人到中年,想快走也走不动了,只能维持自身精神健康,把生活过下去的一个感觉。
在编选小说集的时候,我和出版社的两位编辑有过一些讨论。比如我写了大约二十个短篇,我们一共要从中选九篇。最初我没有选像《于洪》或者《凌空》这些与东北相关的小说。我想要呈现出与以前不太一样的气质。但编辑们很喜欢这几篇,我尊重他们的意见,还是一起放了进来。
但很明确的一个变化是,在2021年我写小说时,我开始不想讲东北那些故事了。那样热烈的感觉我无法再召唤回来。但这不是说我可以去脱离东北书写,也脱离不了,只是没有刻意要去做一些固定的形态。每一篇只是想完成每一篇的目的。比如《漫长的季节》,我只是有点想写一对母女的关系,但这没有必要放在东北的背景环境里。
先生制造:这几年几乎所有围绕你的访谈都是从东北进入的。那个失落的东北,被放弃的东北,工人村往事,历史的伤痕,下岗和再就业。是不是有点谈腻这些了?
班宇:不是谈着腻了,而是我会对自己有一种失望的情绪,是我好像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感觉了,或者我说有新鲜的感受,但这样的感受在东北并不独特,并不奇异。更关键的问题是,如果今天再以东北这个地域元素跟大家说话,到底是还想进入这个元素的什么呢?
现在不是2018、2019年。当时东北突然成为了一个流行的议题,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,无论是宝石的《野狼disco》,还是所谓的东北文学。那时的人们似乎可以与曾经经历过震荡的东北形成某种共识,相互能够理解。
更重要的是,对我自己来说,在2018年我刚刚写作《冬泳》时,我想替一些人说话,想说说我看见的,我经历的,和我在现实经历上想象的那个年代是怎么回事。除了东北工人下岗之类的,除了那些,有一个东西可能隐隐让我特别澎湃。我写了很多过去生活热闹的场面。比如写《盘锦豹子》的时候,里面有过春节的场景,那就是曾经姑父来我家过春节,我记忆里最热情的、最热烈的、最饱含的所有人的生命能量的场景,大家那一刻都被调动起来的感情。大家坐在一起嗑个瓜子,看春晚,打牌,对我来说虽然无聊,但是这样短暂相聚的时间,是我觉得过去年代里面很珍贵的一个东西。
但是,我在今天已经无法像那样去追忆时光了。那样的场景,那样的时间,在今天对我来说已经无法起到激励的效果。我今天再给大家怀个旧?这事我说服不了自己。所以我已经不想再用东北这个躯壳去和大家说话。我会觉得有些无效。
这样的变化当然与这三年有关。这三年里,难道大家不是被拉到一个平面上来进行对话和生活的吗?大家都经历了相同的政策。我们的处境在地域上面的差别并没有那么显著。
我不排斥接下来的小说还提到东北,如果我还能在东北的元素里往深里走一步,有新的东西说,我一定会去写。我只是不愿意被定义成为一个东北作家。
先生制造:不过,即使你想往前走,但是媒体,或者说大众和读者的框架,他们依然是把你框在东北里的。我看到豆瓣上的一个评论说,他能看出东北意识在有意识减弱,也在尝试多元化写作,但纵然如此,他最爱的还是东北血统纯正的《于洪》。
班宇:哈哈。当然我也有一点感受。当时我的写作一定是,打引号,吃了东北的一些“福利”。相当于那时候大家都关注东北,然后关注到我的写作。
不过当年吃过的那些“福利”,对后来的我来说,我一定得吐出来。所以即使读者期待继续读到那样的东北故事,我依然不想按照原来的语境继续那样说话了。也可能以后会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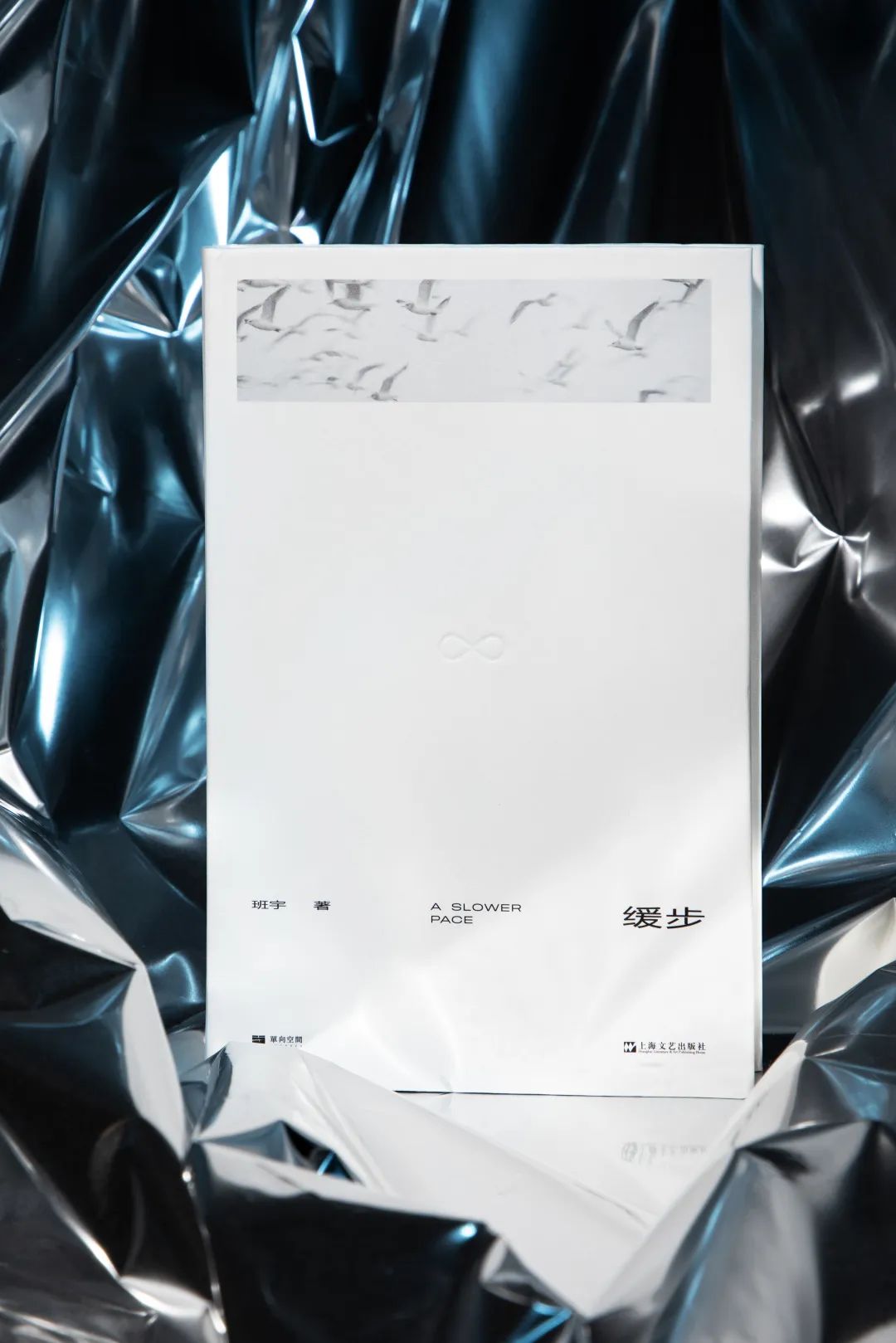
揉成一团的湿润的脏抹布
先生制造: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。今天想来,2019年恰好是你当时事业上的一个高光点。你出了第一本书,受到明星的推荐,获得很多关注,很多奖,参加过一些名利场。但很快就到了2020年,一个改变了所有人生活的时间节点。感觉你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经历了这些。如果让你站在今天回头看,这三年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记?
班宇:在采访前我也想了一下。过去这三年,就对我个人来说,我回忆自己的生活,我的时间,好像是混沌的,一片模糊的。
但与之相比,公众时间或者社会时间在我脑子里却是清楚的。我差不多能记起来这三年疫情期间反复出现的很多事情,很多新闻。但惟独没法解释我个体这三年的生活。就像是这三年的时间成为了一个揉成一团的湿润的脏抹布,它擦不干净任何的东西。
就比如2019年,我们见面的时候,从年初到年尾,我的记忆非常清晰。我那时时刻在提醒自己,不要被各种各样的活动打乱写作节奏。因为我很少经历那么频繁持续的出差,19年我去了南京、长沙,南昌,上海,去了各种各样的书店,每次一去至少要耽误在路上三四天的时间,一天去活动,然后可能见到朋友或者有什么事待一天,然后回来了,我没办法写作。我特别恐慌这件事。但是因为有这种恐慌,其实我当时还保持了一定的写作密度。
我还记得2019年的6月30号,那天我在南京参加一个活动,还有王占黑,大头马,郑执,几个好朋友都在活动上,我们一起喝酒聊天,大家都很开心,喝了很多。喝完我有一点抑郁,30号过后,我不知道为什么,明显感觉到世界变得好像不太一样,那时候还没有发生疫情。下半年,我就开始调整状态,重新找到写作的感觉,也把《逍遥游》定好了。
我也清晰的记得,新冠病毒刚刚被大家所知道的那一瞬间,2020年春节前,我正在沈阳西塔,那是朝鲜族一条街,我在和几个朋友吃饭。那时候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情,不过没把它当成一个很大的事,只觉得它在小范围内传播一下就过了。一周后我们都知道了武汉封城的消息。从此之后,我整个人就开始了近乎三年的眩晕状态。
先生制造:和其他几个出身东北的作家相比,你一直还留在东北生活。你在沈阳,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新冠爆发对你产生了非常切身的影响?比如你辞去了做了十多年的出版社工作,这和新冠有关系吗
班宇:我在2020年的八九月辞职的。从现实原因来讲确实和疫情相关。那时候我在一家古籍出版社,因为疫情,印刷厂纸厂都停工了,但还是给工人发工资,他们就会和我们说,把欠的款都结了。另一方面,书店也停了,网店和实体店都回不来款。上班开始有点赔钱,也不发薪水。我得不停地去垫钱,去负责一些日常开销。
这份工作我已经干了十多年了。以前我会觉得,有一个安稳的工作,业余时间再创作也很好。但现在觉得,也许作为一个作者,我必须要承受一些不安稳。另外我也实在不想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了,就想研究自己的事,看看书,写小说。
现在我自由职业两年了。我也下岗了,哈哈。
我对疫情有非常明显的感知还是在2022年沈阳“封闭式管理”的时候,从3月底开始到4月中旬,比长春和上海封得其实都早。不过东北没什么声音。我有一个朋友是长春一家电视台的记者,他每天能够正常出门去采访。当时他说,上海经历的所有不愉快的事情,长春都经历了。不过长春没有很多声音,就好像变得有点软弱,大家想的第一件事是先把我自己的需求解决了。
有天他发给我一个视频,是说长春封着的时候,群众自发成立了“黑市”。因为物资不够,当时晚上十一二点,在一栋下,有一群人去买鸡蛋和橘子。价格贵一点,但没有特别离谱。最让我觉得诡异的是排队的这些百姓全都戴着口罩,前后间隔两米,特别夸张,依然沿用了日常的那一套规则。
如果说我经历的,当时封沈阳,其实没有那么严格,要求人们不能在道路上行走,每天在小区里面做核酸,听见一个大喇叭在喊,然后会发现每天做核酸的人都比前一天少。没有经历物资短缺的情况。还好封的时间短,以及之前给了信号,大家都囤到菜了。
先生制造:那段隔离生活你们具体是怎么过的?隔离对你和身边人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?
班宇:当时我们一家人一起隔离,我每天都觉得耳边的声音特别多,因为女儿一直在说话。她没法去幼儿园。当然我那阵子就不太能工作了,但冲突也让我们变得更亲密,而且孩子也能让我们维持一种相对规律的生活,这也是有小孩的好处。她早上要吃饭,我们就一起吃饭。我开始学做很多的菜。封城期间我能干的最解压的一件事就是做饭,每天都上抖音快手搜一些菜谱。比如油焖大虾。我也干不了别的,就是在厨房做菜,默默把这些菜准备好。
我后来找居委会开了个证明,想离开家去工作室住。我就说我有个稿子要得特别急,四月初就要交,我还没写完,想去工作室写。然后我就签了一张条。非要出去的话还是可以出去的。当时在家里待了十多天,我已经待不住了,只想出去透口气。但后来知道有一些地方封得更久,有的甚至到了一百天。我心里一惊,几乎不能想象。
封城结束后,我和家人一起出去玩了一趟。回来就会有人给我打电话,问我的行程,你是不是去过哪里?我说对。然后他问,你家庭地址是哪儿?就只有这两个问题。有时我会接到四五个电话,都是问这两个问题。不过打来的机关很奇怪,社区,派出所,还有一次是法院,第一句话我是法院的,我来调查一下前两天你是不是坐哪趟飞机,是不是从厦门回到沈阳,我说对,他又问,你家庭住址在哪里?我问怎么是法院打来的。他说我们也不知道,只是接到了上面派下来的单子。这个数据的单派下去,派多少次是什么,怎么去流通机制,他们都不知道。
然后在2022年的1月4号,我交了《缓步》的初稿。编辑用了一段时间,3月份确认完稿子。但这本书出版方是上海文艺出版社。紧接着是上海的事情,人没办法去办公室,所以拖到实际出版的时候已经是11月份。
我觉得去年一年我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消耗感,就是被这一年大大小小的事情不断的消耗折磨。
小说除去语言之外,
我们到底要谈论什么秘密?
先生制造:这些生活里的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?比如你有在考虑以新冠作为小说创作的背景吗?我们看到之前王占黑的《没有寄出的信》,就是以上海封城为背景的一篇小说。
班宇:我觉得落笔越来越艰难。这是很现实的事情。当我们经历过这一切,如果还写一些轻松的风花雪月的那些东西,意义何在?有什么价值?我觉得每个创作者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,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回答。
我也看到了占黑的那篇小说。她找到了一个办法,一个目击者的视角。那时候我也和她聊过,小说的主角原型就是她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。她在去年春天经历的一些事情。这对她冲击很大,这样强烈的冲动也成为了她书写现实和虚构的一个通道。
但是让我直接描述,我现在写不好。我还没有消化过去的这三年,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它。
先生制造:你之前还谈到,新冠的发生似乎还造成了一种“审美的断裂”。这具体指的是什么?
班宇:比如说,我现在再看卡佛,再看美国中产阶层的情感爱欲,我好像没有以前那样喜欢了。
这两年我开始系统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,看了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,《地下室手记》。原因之一是我想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是怎么结构起来的。之二是我对于他的思想里不断在打架,不断有各种声音出现的这种现象,我觉得做得很好,关于道德和宗教的讨论,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这也是我前两年不太关注的问题。
我也在想,小说除去语言之外,我们到底要谈论什么秘密?这个事我这两年想的多了一点,是要谈论宗教和道德,还是谈论欲望?这似乎是除了故事情节之外,好小说都必备的东西。
先生制造:那么现在呢?当生活转向后,当疫情走向终点,你觉得一切有什么变化?
班宇:12月15号,我印象特别深。我之前出了趟门,12、13号回到沈阳。我去厦门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。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婚礼了,有很多朋友去,男孩是沈阳的,特别开心,我很长时间没被两个人这样爱情时刻现实生活感动,因为我跟我的同龄人,我的同学,基本上都多年前就已经结婚了,都有孩子了。婚礼现场我跟朋友聊天喝酒,虽然大家会有一些隐隐的担心,说已经开放了,厦门会面临什么局面?但大体上,我觉得现场的人心里差不多都是暖暖的一个状态,一种回到正常生活的状态。
回来之后,我妈跟我说,家里有小孩,你在工作室(隔离)住一下,我当天晚上住在那里,我觉得没问题。但是沈阳感染已经很严重了,我的小区里面已经感染了将近一半。我准备第二天回家跟孩子一块住。但醒来,我发烧了,一测就两条杠。我想孩子可不能发烧。我就在工作室里自己住了一周。那一周特别难熬,嗓子特别疼,吞刀片,折腾了一周多,网上说盐蒸橙子什么的,我也试了试,没什么用。
我听到了一些令人忧伤的事情,一些人的去世。所以到今天为止,我依然没有一个欢快热烈的心情,好像这一切仍然挺沉重的。
过去这一年,我实在过得太不规律了。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:幼儿园老不能开园。我的女儿就只能在家里上网课——对,幼儿园也有网课。还有留作业录视频交作业什么的,需要家长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但我们也理解幼儿园,他们也想正常开园。甚至很多幼儿园都因为不能开园黄掉了。
前两天,我和女儿聊天,经历了很心碎的一个时刻。我跟她说,你今年要上小学了,现在也放开了,9月份之前,爸爸可以带你出去转一转,我们可以去迪士尼,或者想去看海都可以。
我女儿说,再等一等,现在咱家还有人阳了。
我说我是阳了,我姨也阳了,但是我们都好了。
我女儿又说,但是外面还有病毒。
我突然因为她的这些话感到心碎。就好像小孩对这些事也有自己的认知。她会觉得有病毒就是危险,不出去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
因此,我也没有办法对未来期望太多。我的愿望很简单:只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变得规律,想要有一个稳定的读写的时间。


Weibo 先生制造 WeChat 先生制造
© 图文版权归《时尚先生》杂志所有。